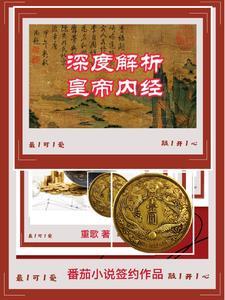极速全本小说网>当时年少春衫薄全文阅读 > 第7章(第1页)
第7章(第1页)
苗人凤就暂时在客店裡住瞭下来,南兰自然和他一起,安全起见这段时间两人就住在一间房裡,同吃同睡。
苗人凤双腿无法走动,多有不便,但他有什麽事大多都是让小二帮忙,若不是南兰自己主动揽下瞭一些类似端药和饭菜的小事,他是绝不会使唤她一点的。
在苗人凤看来,南兰已是他的妻子,他需要珍爱她、保护她,让她快乐没有忧愁,唯独不是行使所谓丈夫的权力。
从前她是金尊玉贵的官傢小姐,日后嫁给他亦是如珠如宝。
苗人凤是个性情内敛的人,讷于言语,敏于行动,这些想法他不会直白地说出来为自己邀功,隻会自然而然地去付诸实践。
譬如当下他便默默地做著这在他看来实在微不足道的小事,向来神情冷肃的脸上微微温软下来,深沉的眼眸流露出柔情注视著南兰。
看她不紧不慢拈起一颗颗蜜饯,蜜色的糖浆沾在她纤长莹白的玉指上,朱唇轻啓,贝齿洁白,隻是吃东西都那样斯文又秀气。
雅致天成,般般入画,像一副赏心悦目的美人图。
南兰察觉到苗人凤目光,抬眼看来对上他的眼睛,便微微笑道,“一直瞧著我做什麽,你也想尝一颗试试?”
说著指尖拈著的那一颗蜜饯便被她亲自喂到瞭他的嘴边,苗人凤便顺势张开嘴由著她微凉的指尖抵在他唇边把蜜饯喂进去。
“怎麽样?”
苗人凤将这蜜饯嚼瞭嚼咽下去,点头道,“……好吃。”
他向来不喜甜食,但或许是她亲手喂的,又见她吃著喜欢,于是到瞭他口中好像吃起来也觉滋味甜蜜又不腻味。
南兰唇边的笑意更深瞭一些,“这是沧州的特産,金丝小枣做的蜜饯,我从前生瞭病喝苦药汁子,向来最爱吃这一口。”
苗人凤是个敏锐的人,注意到她话裡的从前,便温声问,“你从前来过沧州?”
从他们在这间厢房裡说定婚盟也才过瞭五天的时间罢瞭,但他们除瞭彼此的名字和大致的身份外几乎对对方一无所知。
苗人凤不知她这个官傢小姐的父亲做的什麽官,出身的傢世为何,南兰也不知他这个江湖人士到底是豪侠还是盗匪。
因此这并非刻意打探,应该算是增进瞭解的傢常闲话。
南兰也没有隐瞒,隻是脸上的笑意渐渐淡去,“十岁那年父亲考中瞭同进士在京畿为官,我就跟著来瞭京城,直到十五岁才跟著父亲外放回瞭江南。”
是瞭,沧州离京城已经很近。
苗人凤听瞭不觉得有什麽问题,见她神情隻以为是想到刚刚丧命的父亲,而南兰这一番话也的确没有半点虚假。
但倘若苗人凤是个熟悉官场规则的人就会知道,刚考中最末等的同进士就能在京畿为官这件事有多不寻常。
其中定然有许多微妙之处。
但他不知,而在南兰又亲手喂瞭他一颗蜜饯到他嘴边后,苗人凤就更没那麽多馀的心思想这些旁杂的事瞭。
睡前南兰往窗边走去,窗户原本隻留瞭一条缝隙透气,但之前叫刮的一阵狂风吹开瞭。
北方的冬日实在严寒,即使屋裡烧著炕,夜晚若是不把门窗关紧些,隻怕是要染上风寒的。
夜色渐深,万籁俱寂。
建在官道上的客店周围没有其它人傢,隻有一望无际的覆盖著莹莹白雪的平原和稀稀疏疏栽种的几棵松树。
窗前就正好有一棵。
树尖已经比两层楼的客店还要高上一些,形状往两边卷翘的枝叶被厚厚的雪压的弯弯,雪顶含翠看起来颇为雅观。
关窗前南兰赏景般漫不经心地淡淡扫瞭一眼。
“嘎吱……”
就在这时几乎与夜色融为一体的雪松突然传来一声细微地似树枝断裂的响动,晶莹的雪簌簌地从枝上落瞭下来。
南兰放在窗棂上的手顿时紧瞭紧,而原本放松地坐在床上的苗人凤则忽然抬头目光极为锐利地看过去。
房间裡依然是那麽静,但气氛仿佛一瞬间紧绷起来。
苗人凤知道此时正有一双眼睛在暗中窥看著他们,南兰也知道,甚至他们两人其实心中都早已预料到这天的到来。
杀人者人恒杀之。
被杀的那些江湖人自有师门亲人友人,迟早有一天会来寻仇。
换作从前苗人凤是全然不惧的,就是如今一双腿还瘫软著他也大可安然地坐在那儿静观其变,如果隻有他一个人的话。
可现在南兰还站在窗前,暴露在敌人的视线裡。
因此现下苗人凤率先沉声开口打破瞭这场无声的僵持。
“贵客大驾光临,不如出来一见。”
说这话的时候苗人凤紧紧盯著南兰就站在窗前的身影,手裡则已经握上瞭她之前卸瞭放在枕下的一支簪子。
隻等南兰有任何危险,就立刻出手。
被他严阵以待担忧著的南兰直面著可能到来的危险,始终神情淡定自若,冷静注视著雪松上传来异动的地方。
她的确不会武功,但她的心性并不似外表那样弱不禁风。
罕为人知的是本是大傢闺秀的她其实在十四岁那年就已经历过一场远至回疆的冒险,那时她都未曾惊慌失措。
而如今四年后的她,又刚刚亲眼目睹瞭这世间最血腥最残忍的一场屠杀,已很难想象能再有什麽事能让她恐惧。
在南兰的注视下,来人或许真非喜欢躲藏偷袭的阴谋小人,苗人凤话音落从茂盛掩映的枝叶间就出现瞭一个披麻戴孝的身影。
从窗内投射出去的灯光照亮瞭他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