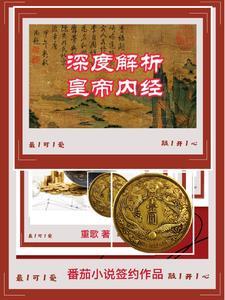极速全本小说网>曾听旧时雨 岑听南 > 第66章(第1页)
第66章(第1页)
若她不曾出现,不曾同他一般沉溺其中,他此生也不会对谁做出这样的事来。
他一时沉默下去,看着她远山般的眉目渐渐因动情染上色彩,呼吸静了静。
在外头这般训她,到底还是太孟浪了些。
等此间事了,不如下次带她去李璟湛的行宫。那里有一处温泉,白雾升起时她若在里头,一定很美。
岑听南趴在他的腿上喘着,像口鼻都被夏日朦胧的气息罩住,呼吸不得。
她微弱地动了动,意图如同花路过春天那样离开他,却被横生出的,坚硬的枝节钉在原地。
这是什么?
“别动。”他却将她换了个姿势,面对面跨坐着,要将她渗透似的。
他的声音仍旧是那样冷而疏离的,好似这样的惊涛骇浪只是她一人的兵荒马乱。
绵中带硬的一次相遇,瞬间叫岑听南意识到了这是什么。
懵懂而晦涩,闪电击穿乌云般震着她。
岑听南弱柳扶风地靠在他怀中,乖觉承受着这场风暴。
被她这样一勾,顾砚时方才还未平复下去的野性又跌跌撞撞闯了出来。
他环着她,颠簸着动荡着,带给她更多的风浪与未成形的黑暗。
潮热而生猛的气息裹着岑听南,热烈的空气如同湖水一样弥漫,闷着、压着、无声喧哗着。
她又热又痒,软得没有章法,胡乱攀着他,想躲开这奇怪的感觉。
身子无意识蹭着,拧着,舒服着难受着想寻一个解脱。
可顾砚时又不肯给她这解脱。
他拍在她疼痛的地方,哄骗似的,哑着嗓子道:“乖一些,娇娇儿。还不是时候。”
“……嗯,子言,好难受。”话一出口,岑听南被自己娇软的声音吓了一跳。
这样媚,这样……羞耻。
顾砚时的腿太长,她这样跨坐着脚尖落不了地,从脚趾到小腿连带着整个身体都紧绷着,被他搂在怀中,一下又一下抛起又落下。
隔着亵裤,隔着外裙,浅浅地为她止着渴。
凌乱的发丝贴在两鬓,岑听南有些失神地想,她此刻会不会很丑、很失态呢?
顾砚时却好似捕捉到她情绪似的,替她拂开额边黏连的发丝。
“真乖。”他喉结滚动,扯开自己的外袍,抚上她脸的手指暴起青筋像是用力压抑着什么。
他的脸上有着疯意弥漫的平静。
可他的声音与动作却仍旧温柔而克制。
顾砚时捧着怀里的小姑娘,像捧着他的至宝。
第30章灯火下楼台(1)
那日过后,岑听南将自己关在房中,不肯见顾砚时。
每回同他做完那样的事,她只觉得不自在。她想不明白这样的关系,更想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喜欢这样奇怪的事。
他们就像走在孤月底下的两个人。
一个在前头慌不择路地跑,一个闲散地跟在后头,行有余力地追。
仿佛已成了彼此秘而不宣的快乐。
但的确有些荒唐事,是要同他这样看起来清疏如明月的人做,才有滋味儿的。
那日后头起身时,他还拎着被自己濡湿的外袍,意味不明地朝她笑,指着那摊扎眼的水迹云淡风轻夸她:“我们娇娇儿真厉害。”
……这是能用厉害形容的事儿么?
气得岑听南只想狠狠咬在他的喉结上。
若不是他那样直愣愣地支着,两人之间隔了一层又一层的绸缎,怎会这样难勘。
回想起那日种种,岑听南一张脸红得反复,惹得琉璃在一旁悄悄端详她好几眼。
岑听南连忙捧着冰镇的紫苏饮子用了一大口,又拍拍自己的脸,心想今年才六月底,怎么就热成这样了。
而顾砚时不知是习惯了,还是体贴她的复杂心绪,只在门外站了一两回,见无论如何逗她,都仍躲起来不肯见,也便随她去了。
一连几日,又是住在宫里头,连相府都没回。
琉璃见她一碗冰饮快见底了,连忙道:“我的好姑娘,你可少用些吧。纵使相爷今日不在,也不能这样贪凉。”
“他今日也不回?”岑听南一面松了口气,一面又有些失落,“我用什么,同他在不在有什么关系。”
琉璃暗笑自家姑娘嘴硬,面上却不戳破,只苦恼道:“没关系么?那日主子们游湖归来,相爷却把奴婢好一通训呢。”
岑听南:“他敢?我的人他凭什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