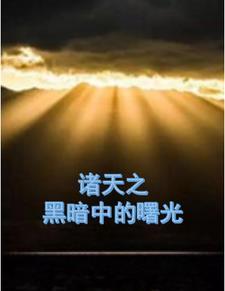极速全本小说网>我的老公是女生 > 第30章 现实(第1页)
第30章 现实(第1页)
又一日清晨时分,金缕旭光方入帘隙,花非若又自梦中醒来。
在梦里,棺中的女帝安然静卧,犹如一缕沉睡的幽魂,而他就在棺外看着女帝,波澜无惊。
却在醒来的刹那间,他又成了躺在棺里的人,心门也就在这骤然间迸生一阵骇跳。
醒转来,营帐里的光景倏忽入眼陌生,却旋即又渐而熟悉,心跳也因之渐而落缓。
心跳归复于平缓后,花非若终于得归平静的看着眼前这一切。
虽仍有无数疑窦盘桓心头,但那三日的恍惚既过,激烈反抗过的心也只能在暴雨过后变得平静。
空躺了良久之后,花非若才渐渐觉得自己“活”了过来。
起先支持着他积极行动的那个念头死绝之后,在这无可回避的现实面前他也只能重新开始思考后计。
花非若强撑着一把绵软无力的身子坐了起来,又看着帐里的景象愣了好一会儿,才站起身来,漫无目的的走到了桌前,又止步,不知接下来该当如何。
当下辰时,伺候的宫女轻步入帐来,却被呆站在桌前的女帝吓了一跳,连忙纷纷伏身行礼。
“奴婢拜见陛下。”
花非若怔怔然的垂眼看着跪在自己面前的三个宫女,思绪迟缓的转了一转,才哑声道:“起来吧。”
宫女们又纷纷起身,领头的那一人上前来,颔询道:“可要伺候陛下梳洗更衣?”
梳洗更衣……
女帝默然良久。
“陛下?”
花非若回神,又看了宫女们一眼,才低低应道:“好……”
闻知女帝醒转,荀安立马赶来帐中,是时女帝正坐在镜前,任宫女们梳盘髻。
女帝似乎是入神的瞧着镜中的自己,而丝毫没有留意他的到来。
直到荀安已来到近前行礼,花非若才后知后觉的转眼来瞧了他。
“起身吧。”
原本满为欣喜的荀安,见女帝此状又不禁担忧起来,站起身后持默了片刻,才小心翼翼问道:“陛下可是觉哪里不适?臣郎这便去唤军医来?”
花非若摇了摇头,“没事。”
“昨日军医为陛下诊脉时,也说陛下醒转后还该再留意留意,还是喊军医来看看吧?”
然而花非若还是摇了摇头,些许木讷。
荀安蹙眉而默。
“他呢?”
女帝虽未明问,荀安却已知她问的是谁,默了片刻,思索着没立刻答上。
荀安没答,花非若又瞧了过去,再次问道:“潮余呢?”
虽然现在他仍有些恍惚思绪不大灵活,却也大概思索能知,昨日潮余带他闯出重围、去至海边此事在旁人看来必是大有异端。
“你们没将他怎样吧?”
女帝急问之下,荀安纵是不情愿,也只能老实交代:“回陛下,潮余眼下在西营,囚于笼中。”
了然潮余所在后,花非若低低应了一声,也略略松了口气——还好没怎样。
正好此时宫女也为他理好了髻,女帝便起身来,一言不的出了此帐,由士兵引路去往关押潮余的地方。
此时慕辞坐在笼中,倚于一角,百无聊赖的拨弄着挂在自己腕上的镣铐,心绪沉沉。
他还是有些担心昨日大为反常的女帝,也不知他究竟是为邪术所惑,还是另有其他……
“陛下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