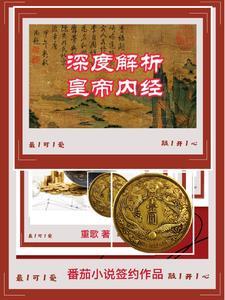极速全本小说网>折妻全文免费阅读笔趣阁番外 > 第237章(第1页)
第237章(第1页)
二人相拥而泣的那一刻,沈幸叹息着走上前来,轻声安抚道:“久别重逢,你们该高兴才是,宫里不能见哭声,把眼泪擦干,我们先回去。”
“好,我们回去……”谢凝强忍着泪意,哽咽地点着头,一双手紧紧地拉着玉盏,始终没有松开。
玉盏擦了擦眼角的泪,微微颔首,无声地向承德道了谢,随后与谢凝互相搀扶着往宫门走去。
望着她们渐行渐远的身影,承德的心中泛起了一股莫名的怅惋。这时,耳边响起了沈幸清润的嗓音。
“谢谢你!”
承德心头一滞,缓缓收回视线,抬眸的那一瞬间,眼底划过一抹转瞬即逝的惋惜。
“离京的日子定了吗?”
“定了,就在三日后。”将他的怅然看在眼里,沈幸的眸光渐渐变得幽深。
“这么快?”惊讶之后,心头涌起了一阵强烈的失落。谢凝入京那日,他以为往后还能在宫宴上相见,却没想到沈幸竟然要辞官归隐。
他们走的如此着急,而他宫务繁忙,怕是没机会送行。出了这皇城,他们此生便再也不能相逢了。
喉间泛起了一股强烈的酸楚,可他的身份不容许他有任何失态,只能压抑地捏紧手心。
“就此别过,保重!”看着承德眼底的克制,沈幸眸光一紧,微微颔首后,立刻起身去追已经走远的谢凝。
沈幸追来时,恰逢宫门开启。望着等在宫外的清越,谢凝忽然顿住了脚,若有所感地转过头去。
悠长的宫道上矗立着一道寂寥的身影,看着承德仍站在原地,本就泛红的眼眶又起了一阵湿润。
有些感情注定无法回应,甚至连当面道别都是那样的不合时宜。
看着她眼底流淌的悲伤情绪,沈幸伸手揽住了她的肩膀,嗓音轻柔地说道:“走吧。”
两旁的守卫都在等着,他们不能逗留,只能强忍着悲伤,迈着沉重的步伐,一步一步走向她所追逐的自由。
坐上马车后,看着瘦弱的玉盏,忍了许久的泪终于能够肆无忌惮地落下来。
一别经年,人事两非。明明有很多话要说,可还没开口却又双双哽咽、未语泪先流。
知道她们需要独处,沈幸并没有跟进去,而是和清越一起坐在了车头。
即便车轮滚滚,隔着一道帘幔,他仍是听见了车内的啜泣声。
回到布庄后,谢凝和玉盏独自待了一夜。第二日,她眼眶红肿地回到了厢房,迎着沈幸关切的眼神,她苦涩地垂下了眼眸。
“玉盏不肯跟我们回江南……”
彻夜长谈后,她明白了玉盏心里的苦,也理解了她的执拗。想到玉盏的心愿,她伤怀地叹了口气,缓缓抬起头来:“她想带着清衡的骸骨回漠北。”
她想以未亡人的身份为清衡扶灵回乡,想去看看他长大的地方。纵然那是个黄沙遍野的苦寒地带,她也甘之如饴。
夜色深沉,烛光昏暗,她的眼神却分外明亮,眼中凝聚着她从未见过的坚强。
看着那个坚毅的眼神,谢凝就知道自己不可能说服得了她。
可对于玉盏,她的心中始终充满了亏欠。这一路走来,玉盏为她承受了太多苦难。
听了谢凝的话,沈幸陷入了沉默。清衡为她丢掉了性命,而她虽侥幸活着,却也甘愿献祭余生,翻越重重沙海,将他送回故乡去。
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他心中既钦佩又感动。
“既然她心意已决,那就让她去吧。”
每个人都有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他们如此,玉盏也是。比起劝阻,他们更该做的是认同和祝福。
离京的前一日,沈幸带着谢凝和阿粟去了一趟皇陵。
他远赴江夏之时,曾向昭仁帝呈上了一封请愿书,请求他为怀王昭雪,还他一份清白。
后来,昭仁帝果真揭露了先皇辞世的真相,处死了陈吉,洗刷了怀王身上的污名,将他的尸骸迁入了皇陵。
站在庄严的墓碑前,望着石碑上镌刻着的那一行碑文,往日种种如走马灯般一一重现。
他曾答应过怀王,有朝一日一定会还他清白,如今他总算是不负所托,若他在天有灵,此刻也该安息了。
他正心有戚戚之时,身旁的阿粟指着高大的坟茔,好奇地问道:“爹爹,这是什么?”
看着他天真烂漫的神色,沈幸缓缓蹲下身子,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头:“这是一座小房子,里面住着爹爹的朋友。”
“他怎么不出来呀?”阿粟奶声奶气地问着,眼底满是疑惑。
闻言,沈幸呼吸一滞,喉间泛起了一抹苦涩。可迎着阿粟充满探寻的眼神,他还是语调轻柔地答道:“爹爹的朋友睡着了,所以他不能出来。”
“那我们,什么时候能见到他呢?”看着父亲忽然泛红的眼眶,阿粟的面上出现了一丝困惑和苦恼。
见状,一旁的谢凝将阿粟抱在怀里,嗓音温柔地哄道:“他太累了,我们让他多睡一会儿好不好?”
“好。”被谢凝抱起的那一刻,阿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乖巧地搂住了她的脖子。
一阵寒风吹过,枝头的树叶落了一地,发出了哗哗的响声。沈幸站了许久,直到铜炉里的香熄灭,才牵着谢凝的手缓缓离去。
步出皇陵时,他们看见了一个身着素色锦袍,站在树下诵读经文的少年。听到守陵地士兵唤了他一声“安王”,谢凝才意识到那是崔琰的表弟,曾经备受瞩目却因年纪太小而错失皇位的六皇t子。
许是察觉到了她的注视,远在树下的安王忽然回过头来,瞥见站在台阶上的一家三口,他的面色一如往常,没有任何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