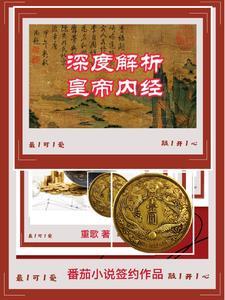极速全本小说网>大家族 > 第70章 请半仙破局(第1页)
第70章 请半仙破局(第1页)
对于文明程度和文化教育欠缺,仍被封建文化意识形态控制和引导的水淀村民来说,茶余饭后,议论东家、说说西家,已经成了他们生活的常态。
在那样一个信息极度闭塞与匮乏的年代,一个寡妇女人的一点事情都会被千百张嘴巴不断地咀嚼,不断地加工,不断的传说。
在水淀村民来看,经过加工的海棠肚子如何大了?有了很多版本,但主要是两个,一说是杨大麻子还魂给搞大的,也有的说是海棠和来喜疯疯癫癫转悠时,让哪个缺德的野汉子给害了。
海棠的大肚子又成了水淀村继她的青砖瓦房之后的又一热门话题,人们都在猜是哪个缺德男人干了坏事。
杨二爷听说海棠肚子大了,脸色铁青。
他召集了杨家氏族里有辈份的老人进行商议该如何处置。
杨家的长辈们一个个抽着烟袋,大眼瞪着小眼,都没话说。
沉寂中,倒是杨二爷先开了口:“这海棠一个寡妇,居然大了肚子,这杨家的名声可在淀北淀南就坏了,这以后谁家还敢娶杨家的女人,谁还愿意把自家的姑娘往杨家嫁。”
“对,对,这海棠就是不守妇道,那时候还勾搭我哩。”不知啥时候,已经被踢出杨家氏族长辈行列的杨五爷扒着门,贼眉鼠眼地叫嚷着,他的光脑瓜顶上一道新疤痕特别扎眼。那是上回偷看海棠被来喜给开的瓢!
杨六爷看着杨五爷脑袋上雪白的疤了,虽说是兄弟,但对杨五爷所作所为的卑劣小人行径感到很气愤,他有些恶心,于是忿忿不平地说到:“五爷,这咋说的,海棠的肚子是不和是你有关系,按规矩,你是要被沉塘的。海棠可是个疯子,按理说是不受牵连的。”
“六子,你咋血口喷人,我五爷咋会做这不是人的事儿,不是我,真的不是我。老六,你栽赃陷害我,你和海棠究竟是咋回事?”说着,杨五爷一下子跳进了门槛,站在门里,歪着个脑袋,插个腰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活像一只天天向人们喊着“看我像不像人呀”的豆鼠子。
厚道的杨六爷看着杨五爷的这副德行,把使劲吸了一口旱烟,便一边在炕沿上轻轻地磕着烟锅里的烟灰,一边不紧不慢地说到:“五爷啊!做兄弟地哪敢说呀,这不是你自己招的嘛!对啦,你脑袋上地疤了咋来的?”
“二爷,我和海棠没瓜葛,她肚子和我是一丁点关系也没有。”说完像只老活猴一样噌地窜出屋去就没了踪影。
六爷和其它几个兄弟见状互相看了一眼,噗哧都乐了,接着又都闷头抽起了烟。
杨二爷板着有些青的长脸,咕噜咕噜地吸着水烟壶,阴沉的目光不断从族里几个兄弟有些烦躁表情的脸上扫过。他看清了他们脸上的表情,觉得这几个兄弟都对海棠的大肚子似乎一丁点兴趣都没有。
杨二爷心里暗骂着:“你们家都是挺顺气的,活得劲劲儿的。”杨二爷沉不住气了,他心里就像挂了一串左右摇晃着的秤砣一样,沉沉的,很不安。
在坐的杨家的哥几个哪里知道,杨二爷几天前花了大价钱,偷偷地把方圆百里最知名的风水先生周半仙请到了自家,想让他给看看自家究竟是怎的了?怎么这么不顺!这接二连三的生死人怪事。
从大儿子之死起,杨二爷天天提心吊胆的,连睡觉都不踏实,他真的害怕杨家大院就这样败了。
周半仙到了杨家,煞有介事地背着手,迈着两条麻杆似的细腿,先围着杨家大院走了一遭,进了院子后,又躬着腰,顺着房根墙角,这敲敲,那摸摸地溜了一圈,这时候就差不多晌午了,于是吃了杨二爷备下的大餐。
酒足饭饱之后,周半仙抹抹嘴边的油,便在堂屋的砖地上盘腿打坐,闭上了那双有点斜的死鱼眼,薄薄的没有血色的嘴唇蠕动着,出一种没有人听得明白的声音。最后,那只干瘦的大手在空中划了一个圆圈之后,便直挺挺地指向了屋顶。
杨二爷站在一旁看得舞迷三道的,看到周半仙的手指停留在半空指着屋顶,便微微前探了下身子,恭敬地问道:“仙人可曾现了什么?”
周半仙没有搭理杨二爷,高举着如柴禾棍一样干瘦的胳膊。杨二爷傻傻地站着,望着周半仙,心里越忐忑不安。突然,周半仙高举着的手臂一下子向后弯曲了下去,指着自己身后的方向。
杨二爷心里更着急,本已经罗锅的身子躬得更厉害了,不安地又问道:“仙人可曾现了什么?”
周半仙慢慢张开了那双死鱼眼,眼皮耷拉着说到:“二爷,您家可遇到大克星了!”
“啥克星啊?”杨二爷听到周半仙得话差点没栽倒,多亏三儿子天满眼疾手快扶住了他。
“二爷啊,您家房后有一座新盖的砖房,对不?”周半仙一本正经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