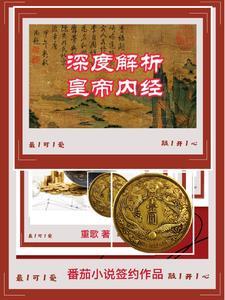极速全本小说网>元朝女仵作柏钰 > 第六十四章 旧人重遇(第1页)
第六十四章 旧人重遇(第1页)
张炎一进门,任羽便一把将他拉过来:“这人谁啊?”
手指着桌上的女人尸体,视线却落在了那人脚底的红土上。
“这人该不会是死在山上呢吧?”
张炎找到机会拍个马屁:“厉害呀!你这么看一眼就知道了?”
任羽嘁了一声,松开手:“你也不想想咱们京城这地方,哪儿能见着红土啊?这东西除了烧陶那块有,就是山上才会有,你那脑袋是用来干嘛了?这么简单的道理都想不到?”
张炎看他这副顺竿爬的得意样子,心里不觉来气。
嘚瑟什么呀你?要是我搭档在,还有你什么事儿?
想到柏钰,又想到他后背的伤,这日子突然一下没了盼头。
张炎将手里的验尸工具包递过去,随后走到一帮仵作身边站着。
任羽上了。
观摩团也围上去了。
相比柏钰手上那新颖的验尸功夫,再看任羽就要显得传统保守多了。
他的动作很慢,却又粗糙,割出来的轮廓也不如柏钰的准确干净。
仵作们见过了不一样的手法,再看此时任羽手头如此普通的手法,顿觉无味,转头就各自闲聊去了。
此时,牢房里的两人久违相遇。
沈大经过那间漆黑一片的牢房,余光中忽然注意到一抹熟悉的身影。
“继续走!”牢头推了他一下。
沈大手脚都上了锁链,想跑也跑不了,刚才那一眼他便已经认出来了,那是何花的儿子。
他未曾真正见过,也不知姓名的孩子。
沈大对他唯一知晓的事,便是他生来就像他娘一样,患上了惧怕阳光的怪病。
若非如此,当年何花也不会毅然决然推开他,执意要独自抚养这个孩子。
牢房周遭散发恶寒,他被单独关在隔壁牢房,跟那人只隔着一面墙。
沈大站在墙边,几次想要跟他说话,却怎么都得不到回应。
就在这时,房门外传来脚步声。
像是有很多人过来了。
走在最前面还是刚才那个牢头,他二话不说,上前开门。
紧随其后的人,沈大见过,正是进城这一路上押送自己的人。
赵元生面带微笑,腰间的玉坠随着步伐轻轻摇晃,牢房里的桌椅常年不经打扫,不知落满了多少尘灰。
但他偏偏就这么坐下了,那身白衣很是扎眼,却还是让人移不开眼睛。
沈大知道他的身份,也很清楚他的到来绝不是什么好事。
“坐吧。”
他的声音犹如深谭里的清水,带着一种压抑,不自觉让人服从。
沈大坐到他对面:“你还想知道什么?”
赵元生也不卖关子,开门见山地说:“就从京城里发生的第一起杀人案说起吧。”
詹青走了进来,带着烛台,身后跟上来的几人手里同样端着烛台,原本阴暗的牢房忽然充斥着光亮。
屋里众人的表情,全都照了个一清二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