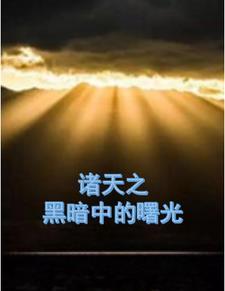极速全本小说网>成缺锌有什么表现和症状 > 第46章(第1页)
第46章(第1页)
“郑时朗,你到底还有多少个秦少爷?不会过两天又有一束花越过我面前送来给你吧。”秦霁渊拽过他拷着手铐的左手,把手铐打开,“送花也该送到报社或者你家,特地送到我面前来,依你的理解,是想表达些什么?算了,是我无德无能,还是栓不住你。”
昨晚的事还没解决,这又来一个覃少爷。郑时朗,你还真是和这个姓过不去了,找个情人还要找个名字和自己爱人那么像的,不嫌膈应?
秦霁渊摩挲着自己手指的指节,沉默了一会儿:“多久了?到底是从哪个我没看住你的早上开始的?”
郑时朗无奈:“我连人家长什么样都没见过。当时匆忙应下来后还说要问问你覃少爷是何许人呢,昨晚事出突然就急忘了。你不喜欢,我不去就是。”
花已经被送上来了。整体配色很阴沉,和郑时朗给外人的印象一致,但显然不适合送人——深紫色为主调,带着几朵染了色的黑色小花,就连包花用的纸都是灰色。绑着一根绀色缎带。
“什么审美,这花放葬礼上我都嫌晦气。这是祝你康复还是咒你啊?”
“我真的不认识他,哪有情人会送这样的花?”
郑老师按下不提的是,前两天收到的花也是和今日一样极端的配色,看着扎眼,像是给他的死亡通告。
但他不想告诉秦霁渊,他气过也就过了,担忧可比怒气沉重得多。
看着这束十分扎眼的花,秦霁渊总感觉好像在哪里见过。是,是报社的角落,那摊白得像纸花一样的东西,也是人造漆喷出来的产物。还有旁边那堆红得发黑的东西,被随意地堆放在墙角。秦霁渊第一次看到的时候就觉得不对劲,却没来得及问他。
秦霁渊把门锁上,一步步逼近郑时朗,直到把他压在床头:“告诉我,覃净屿是不是和村上有关系?”
“老实说,我不知道。”郑时朗朝他支起绷紧的手臂一击,他就失去平衡压在了自己身上,“还有很多话要慢慢说,这样撑着太累,还是躺下来听吧。”
秦霁渊翻身躺到郑时朗旁边,看着郑时朗又一次把掉到地上的手铐捞起来给自己拷上:“或许你真的栓不住我,但我会把自己拷在你身边。放心,秦少爷,这辈子只有你一个秦少爷,下辈子也是。”
他把钥匙抛回给秦霁渊:“这次栓紧点。”
秦霁渊利落地接过钥匙:“别废话。”
“周林最近得知一条信息,二十七将有用于人体实验的重要药品运到码头。近来村上的行动已经转守为攻,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让他再也没有等下去的耐心了。我怕这消息有诈,但周林坚持要亲自确认,怕错失行动的良机。就在她传递信息给我的时候,也就是昨晚,有一个戴着村上家徽的人向我下了周林的死亡通牒。”他找出那张不祥的纸,“我昨晚一时糊涂,竟中了他的计,急急忙忙地去传递消息。所以才这样狼狈地赶到王记药铺,又这样狼狈地见你。”
郑时朗看着“黄鹂将死”四个字,不觉有些愣神。直到拿着纸的手突然攥紧,秦霁渊在他的眼里隐约看到了几分泪意:“我知道我太冒失,可是我想救她啊!我真的想救她,我要怎么办才好!”
他抱紧秦霁渊,把头枕在他的颈窝上,很久都没说下一句。秦霁渊从来没见过他着急成这样,又心疼起来。
秦霁渊不知道怎么安慰他才最好,只能给他足够的时间调节情绪。好在郑时朗也不是会允许自己情绪失控太久的人,不多时语气已经平缓下来:
“不过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困兽犹斗罢了。但就是这样斗,我也要斗出条生路来。”
这条生路,我要斗出来让你们走。
旧楼
行动开始前的这几天,她当做生命倒计时的这几天,周林常常站在窗前,望着后院外的那张长椅。
她在等谁?在等一个明知不会再来的人罢了,临了还是活不通透,故事到了终局竟还成了痴人。红尘中滚一遭,还是勘不破尘世纷纷扰扰,太愚,太愚。
如果可以,她想把时间拉回初见那时,拉回那个开春。她仍旧日日在那看书,仍旧等来连同她握手都脸红心跳的冯清筠,这一次,她一定会选择踮起脚尖,吻上他的唇,同他说:“我们跑吧。”
靠这些年的积蓄,跑到北平去。去读书,去游行,去干什么都好。跑到山水都穷尽了,就卧于一叶小舟,笑看云起。
不过妄想。
她比任何人都清楚,自己何以至今天,不就是因为放不下,所以才走不得吗?罢了罢了,不走也罢了,今日留,或能有明日生。
可她竟是等到了。
他忐忑地在长椅旁踱步,一样是那套褪了些色的藏青中山装,不同的只是没有旧日的诗。远远地从窗边望去,看不清他的神情,只懂他似乎攥着些什么。这样的朦胧也是忐忑的,忐忑的是她周林。
此时再去赴约大抵只会让他更危险,但有些话却是不得不说的。她只犹豫片刻,换了身衣裳便匆匆下楼。
冯清筠说不清自己为什么要来。就像他说不清自己哪里喜欢桂小姐,明明还未相知,也不敢谈相识;明明是自己的一厢情愿挡了人家的财路,只落得一番羞辱。但他还是想来,只为李醇那几句话。他总觉得是桂小姐怕自己涉险故意激他,其实心里早有答案,李醇一点化就更深信不疑。世人皆笑李醇疯子,却看不透他也是痴人一个。
他说过他不是李醇,所以他来。
一时恍神,一个女学生装扮的小姑娘同他擦肩,慌乱间手中的东西被她夺了,他才回神追上去。